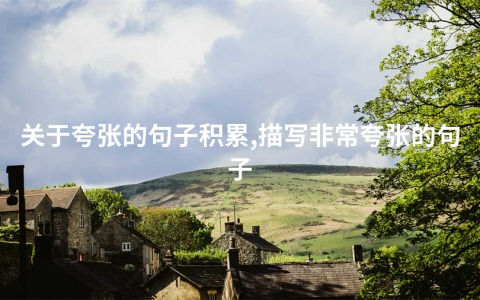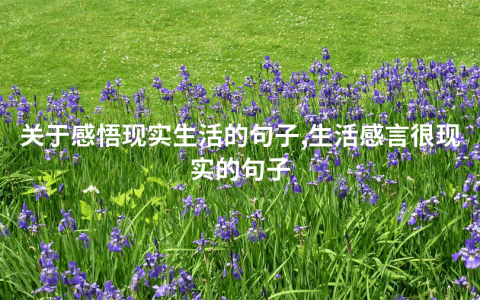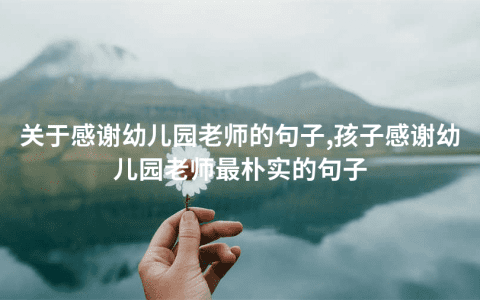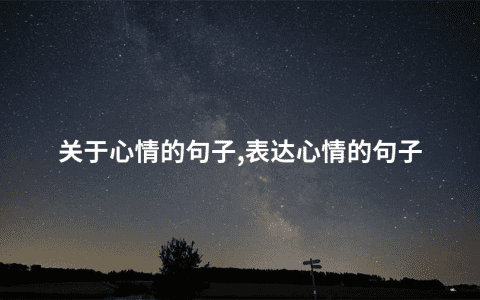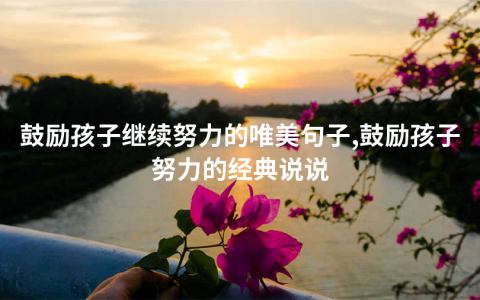关于描写声音的句子精选,描写声音的优美句子和段落
选自《十三邀》文 | 许知远 项飙公号内回复 福利 可领取《人生必读30本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99部》如果说今天中国年轻的学生,你要问他:你父母干什么的;当时在这个小区买这个房子,你的父母是怎么考虑;你这个小区,在你的城市里面,社会意义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与周边的菜市场是什么样的关系;你的学校(上学经历)是怎么一个过程——他描述不清楚,原因是他会觉得这个有点无聊。
因为他觉得重要的是要超越这个东西。他觉得我要考一个大学,所以他对怎么样考大学,他对世界排名非常清楚,然后托福、GRE怎么考,他对那个系统他会非常熟悉。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所谓辩证的关系在里头了,前面我觉得这种超越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没有超越感,你不会对你身边的东西,实践的东西发生兴趣。
但现在呢,有另外一种矛盾问题来了,他只有超越感,他就没有通过超越来回观、回看自己身边的世界。自己身边的世界成为一个要抛弃,要离开的一个东西。
每一个个人,不是一个封闭的、自在自为的一个生物体,而是世界上很多要素的聚合,在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临时的聚合。个人确实是有很多层次的,一个是(作为)纯粹的自我的个人,另外一个是作为很大集体载体的个人。
所以现在一个矛盾是,本来这多个层次的个体,它们中间应该是有紧张关系的,是有矛盾关系的,(它们)大部分时间应该是整合在一起的。
但现在它有个断裂。
一个自己纯粹原子性的个人,有的时候是关心(自己),然后有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跳出来,对很大的一个事件做很宏大的评论,但是他的中间这一层,对这个“附近”他没有兴趣的。他只对他家里头,或者全世界(感兴趣)。
附近的消失,是一个问题。
总体地来讲,现代社会它是都有一种趋势,就是消灭附近。
我对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我不太喜欢,但是新自由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我觉得是存在的,认为市场是万灵的,是一切的解决之道。市场是附近消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认为附近是一种障碍,交易应该是没有摩擦的。
“附近”到哪儿去了?对美团外卖的平台设计师来说,“附近”对他来讲太重要了。“附近”的交通情况,什么时候人流多,什么时候人流少,他要掌握。他把我们本来肉体直接感知意义上的那个“附近”,一下子转化为一个数据化的“附近”。
“附近”不是简单地蒸发掉了,而是转化了,这个转化的背后有资本的力量,是一个技术过程,是一个很多利益的重新组合。它会带来一种新的“方便感”——我要什么就马上来。
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发达,如果5G普及以后,整个交易时间的摩擦会越来越短,即时性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所以“附近”就消失了。
这种即刻性似乎是一种反思能力的下降。因为好像一切东西没有距离了。快递小哥马上给你送过来,如果你不能达到即刻的欲望,你会很恼火,这种感觉很恼火,但你不会去考虑快递小哥跟你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它不是常规的一种关系,因为每一次,每一个即刻,快递小哥都是不一样的人。
换句话说,你就被即刻推着走了,就很舒服地被裹挟了,就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方便下,你就这样“骨碌骨碌骨碌”,一个即刻到下一个即刻,就这样下来了。
(许知远: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野蛮化?因为我们所谓的公民美德这些东西,比如互相尊重,互相同情,都是在人和人的相对更长期的关系中形成的。而这种非常快的不断切换,不需要培养任何同情和理解,人会重新回到或者动物性,或者野蛮化,或者本能化。其实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发生了。
情绪化已经发生了,整个社会已经非常的情绪化,高度情绪化。比如他忽然会对某一件事情非常同情,非常愤怒,好像被伤害了。但那种情绪又很快下去了,因为它不能转化为他的行动。)
你说得很对。所以我一个非常粗略的感觉是:
一方面是原子化、个体化,那种具体而微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比较松散。
另一方面却在信任和意义系统上高度甚至是极度的集中化。比如我不太信任你,但咱们都信任支付宝。我们会对一种抽象系统——当然这个系统是一个很具体、很复杂的技术构造出来的东西——高度信任。因为不信任的话,就不可能有即时性和方便性。
第三个就是最原生的社会关系会本质化。父子关系,也就是代际关系,即靠一种生物学来界定的关系,又重新被认为是个很重要的事。
(许知远:最后一点我印象挺深的。我们这代人以为整个社会会朝向一个越来越个人主义的方式来运转。它不是原子化,而是更依赖于自己的努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更平等,血缘关系的影响会减弱。但是过去几年是剧烈的回潮,我们想都想不到,年轻一代又需要父母来帮他们决定婚姻。)
这个绝对是想不到,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说父母给你介绍个对象,那太掉价了。
听起来很奇怪,一个时间感的变化,怎么会导致出一个婚姻感的变化,但是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他对整体生活的感知会发生变化,所以他对婚姻,对家庭会有一种新的理解。
为什么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会有那种能力呢?因为我们自信能够在“附近”构造出一种爱的关系来。在一个单位也好,哪怕在一个公共汽车上相遇、碰见的也好,我们有自信去构造。
但现在我们好像丧失了这种去构造出一种能够相互信任的关系能力和自信。
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拿这种超社会的生物关系去作为一个意义的基础。一个是生物关系,再一个是理性计算,比如门当户对是通过别人介绍和大量的信息比对。
最大的输家是谁,首先是妇女本身。从精神意义上所有人都是输家,一种被羞辱的感觉,道德上对不起父母,价值上被社会羞辱。这样,所有的人对社会的理解就变得非常单一,所有人在这个话语面前都变得非常的脆弱。
(许知远:我们怎么抵抗,怎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重建个人的意义与尊严?)
一个简单的例子,土著人他不会说一头牛是一头牛,他们认为一群牛才是一。只有到了近代社会,你才觉得我个人是一个个体,是独一无二的,通过对独一无二性的追求,我才能得到自己的尊严和自由,这是一个相当相当新的想法。
我个人倒觉得这个不是出路,个人的意义与尊严出路不在于个人,一定是在于关系。没有一个天然的个人尊严的,没有一个东西在那里。
你不能够去追求人尊严,你一定要建构出附近,重新去想这个关系,建构出关系。
(许知远:我们这代人一直认为自己致力于创造一个中间社会,中间层,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那个社会。包括从晚清开始,从你外公的父亲开始,创造中间社会。到我们40多岁的时候突然发现中间社会的形成是不可能了,或者说本来形成一些又消失了,又重新变成了两个极端,是码农的世界和马云的世界。)
中间的消失就是附近的消失,一样的,都联系在一起。
一方面从经济指标来看,很繁荣的。因为你要把社会理解为是一种消费行为,各种俱乐部,这些都崛起了。但从精神社会来看,中间是很弱的,非常弱。你提的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的问题。
所以会有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一定是两个东西的结合,民粹主义的背后都是精英主义,否则你没有纯粹的民粹主义的。民粹主义都是说一个精英分子说他直接代表民众。民粹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是中间层,所以需要介入。知识分子需要介入,哪怕是词语的一些说法给大家。
(许知远:那你觉得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
他很在地,要有很强的敏感性。对古典的东西当然要熟悉,但是一定要到现在的这个实践当中去。他的神经一定是要跟着时代去跳动的。
你的出发点必须是现在的困惑,必须是大众的困惑,必须是最新的变化。你的出发点不能是孔子说了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了什么,马克思说了什么。现在不能再问孔子当时说的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用,你要问的是,如果孔子活在今天,掌握了所有这样的信息,像他这样的一个思考者,他问的问题是什么,他会说什么,给出什么答案。
(许知远:你现在四十多岁,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驱动去研究?)
一是智识上的好奇,跟所有搞研究的人一样;二是你活着是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活着,你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环境下,你希望对你自己这个生存的环境能够有一些说法。
如果你不能够有这样的说法好像我不能达到一个自我实现,好像真的就跟历史、周边就擦肩而过了。
一方面你知道宇宙有多大,但另一方面你知道,每个个体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哪怕你再渺小。
哈佛毕业,不找工作;自己砍树盖房子,一个人住在森林的人,能否过好这一生?
不吃牛排,也不恋爱。只喜欢看蚂蚁打架、鲈鱼游泳、倾听猫头鹰午夜嚎叫,读取一只鹌鹑的眼神……
你以为他是个怪咖,美国人却说:他教会我们如何度过这一生。
他就是“海外陶渊明”,神级作家梭罗。
网上流传着一句话,如果你看到有人在读梭罗的书,一定要鼓起勇气要他的微信。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喜欢读梭罗的人,值得深交一辈子。
大文豪海明威、托尔斯泰、爱默生、海子,都是他的狂热粉丝,都推荐过他的书。
梭罗说:“时间只是由我垂钓的一条溪流。”
他与生俱来的敏锐智识,如同一位刀客,能帮助他洞见万物的隐秘。
哪怕是一段描写鹌鹑眼神的段落,也堪称文学作品里的绝唱:
所有的灵慧似乎都写在那双眼睛里,其中不只是童蒙的纯真,也有经过砺练得以升华的智慧。这双眼睛是造物者的馈赠,跟它映出的苍穹一样久远。
一个人烤面包,他说:
我小心翼翼,呵护有加。不时翻动两下,就像埃及人照看正在孵化的鸡蛋。
他这样理解自由:
在前行的途中,不因为纤芥之微而改变初衷;早早起床,用或不用早餐,都优雅从容而无丝毫不安。
有人问,一个人住在森林里,是否会感到孤独?他说:
我早已发现,任凭双腿怎样努力,也无法使两颗心更近。
我跟湖中朗声大笑的潜鸟一样远离孤独,跟瓦尔登湖一样不
本文地址:http://naizai.cn/archives/7908
以上内容源自互联网,由百科助手整理汇总,其目的在于收集传播生活技巧,行业技能,本网站不对其真实性、可靠性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特此声明!
题图来自Unsplash,基于CC0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