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岁逃离编制,10 年后我又回到体制内
2013 年,在北方地区某疾控工作了 7 年后,王旭毅然辞职前往英国留学。他辗转于德国、挪威,最后在法国落脚。
目前,他正在法国医学科研中心(相当于国内的中科院)做博士后,下个月,他将去巴黎最大的综合医院之一就职。如今王旭已将父母接来法国生活,「在法国,每年除却十几天公共假期外,我还有 10 周带薪假期,我可以好好陪着他们。」王旭说。
从公卫医学生、到专事肺结核防控的疾控人员,再成为欧洲留学生、法国精神科医院的统计分析师、最后又将在大型综合医院任临床实验方法学家(负责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方法的前期设计等),22 年的医学路上,王旭转变过许多身份。
最终,他又「回到」了体制内,只不过这次是在法国。回望一路,王旭说自己也曾多次崩溃。以下是王旭的自述。
01 从人人羡慕的疾控辞职
2013 年,我辞职了。当时我已经在北方地区某疾控中心工作 7 年,属于结核病控制中心的青年骨干,负责肺结核的防控、流行病学调查等。我的辞职是真正的「裸辞」——我要去英国读书,30 岁的我重新变成了学生。


我在疾控工作时
我工作的疾控中心实际属于省级疾控,在我毕业(2006 年)的前后几年集中考试招聘了几十个本科生及硕士生,之后每年只有少量硕士、博士才能入职。因此我能顺利进入疾控,已经被身边人羡慕。
但那几年来,我的内心很不安,外人很难体会。
其一,是工作内容的重复、枯燥。我发现每年发布的新规、开的会议和去年都很类似,大家的角色都是上传下达,很难有发挥的空间。这个过程中,我的工作意志越来越薄弱。
其二是家庭带给我的影响。我的父母原本在很稳定的国企工作,却在 90 年代双双下岗,为了生存,他们换过很多不同的工种,努力迎接时代带来的人生挑战,前半生过非常操劳。
「平静的海面下可能隐藏着巨浪」,我深知这个道理,就算我是大学毕业,也可能和父母的境遇没有太大区别。
在疾控第五年的春节,我在写完自己的年度工作报告回看了下。报告印证了我的感受:除了年份改变,我每年的工作内容几乎都是相同的,客观地说,我觉得自己成长受限。




我在疾控工作时
我对自我的评价是危机感强、行动力强,胆子也比较大。大学没毕业时,我想不清楚自己到底要考研还是去疾控,所以在本科毕业答辩后直接去找评审团(其中有该疾控中心的主任)沟通,她和我聊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放弃了读研,入职了疾控。体制内,我算是少数很活跃的人,积极推进各种项目,年末聚餐也是我来组织。
可以想象,我这样的性格在体制内会有些躁动。转折点出现在 2011 年,我被派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几个月的时间里学习流行病、生物统计、全球卫生等课程。




我在密歇根学习
我还参与这里的小组科研课题讨论会,这群医学生对于国际前沿科研理论的挖掘、以及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医学实践新方法都非常热衷,学校也给予了他们足够的机会去试错。




我在密歇根学习,参与讨论会
这时我出现了留学的念头:如果不出去看看、不切切实实地走一圈,我想我一定会后悔。
我一边攒钱一边重新捡起来英语,学了大概一年多。刚来疾控的时候我月薪是 2000 多,慢慢涨到大几千,工作六七年后有几万块积蓄,当然要去留学一定是不够的。2013 年,北京出现 H7N9 禽流感,我被安排去基层做传染病防控,这份经验让我拿到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全球卫生专业的 offer,我又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2014 年 10 月,我去了伦敦。
02 辗转欧洲,我来到法国医院工作
在英国一年的硕士生涯里,我通过项目去了德国和挪威的大学辅修,又参加了 WHO 的世界卫生大会。综合过往的经历以及未来方向,我渐渐锚定:我要去 WHO 工作。
在 WHO 工作最好可以掌握三门联合国官方语言。我会汉语和英语,就考虑学习西班牙或法语,这样可以去拉丁美洲或非洲研究传染病。 从 UCL 毕业后,我手里大概还剩下十五万存款,就去了法国读语言班。




我参加 WHO 会议
来到法国以后,没有了全额奖学金的支持,我开始自食其力。我白天上语言课、晚上去餐厅刷盘子,做了两个月,感觉非常劳累。好在我很快找到一个科研公司做实习——负责给法国的疫苗项目寻找中国投资人,帮助他们做项目融资。
我在国内的人脉一直没丢,这份工作正好和我的资源对口。当重新和过去的人紧密联系起来,我发现以前疾控同事已经陆续升职、我的本科同学也博士毕业,进入高校做稳定的教职。他们好像都有了大好的前程,只有我主动抛弃了这份稳定,却也没有闯出什么名堂。
我决定不去 WHO 了,我想留在法国、留在医学系统。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机会。




在法国语言班时的聚会,我是前排左三
一次论坛,我遇到了巴黎五大医学院的校长,表示希望能在法国读一个博士,回归医学系统。在他的引荐下,我开始申请奖学金。负责人给的回复是:「你在英国的硕士只有一年,而在法国硕士需要两年。你需要再读一个法国硕士、直接研二入学。」于是我入学了该医学院的临床流行病学硕士专业。
但直到毕业时我才发现,还是很难申请到对口的博士项目,因为法国流行病学属于纯医学的范畴,需要在当地医学院读至少 9 年,才能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卫领域,因此我没有任何机会。
这一点,当时负责人没提过, 法国的招生简章对招收标准的描述比较模糊,我没有办法提前了解。
彷徨之中,我又开始寻找新赛道。在和法国医生接触的时候,我注意到,法国医院里的生物统计组是由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毕业生组成的,他们都不具备医学背景。每天早上,医生们要和生物统计人员要凑在一起开会,研究怎么将数据和医疗结合起来,但过程其实挺难的:医学生不太懂数据,懂数据的不懂医学,但我两边都懂一点。
这给我了我启发,我是不是可以做那个中间赛道?
于是我换了新的行业:医疗大数据。这是我在欧洲读的第三个硕士,之后的博士以及博士后也和这个相关。
从硕士到博士的这几年,我都是在同一家儿童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实习,为他们做医学数据库的挖掘和分析。如果按照国内医院等级划分,这家医院可能相当于二甲,它根据儿童和青少年的年龄(0~4 岁、5~12 岁、13~17 岁)、病情(自闭症、精神分裂等)划分成不同的住院部,孩子们周一到五封闭住院,家长带他们回去过周末,周一再送回来。




我在法国实习并工作的医院
在法国,儿童精神疾病属于医保全覆盖的范畴,家长不需要为孩子的治疗付钱,所以这里没什么医患纠纷。医院里开设了学校,为孩子定制了课程和训练,由专业人员监督完成;如果孩子需要 24 小时监护,医院会给政府「下订单」,政府来找看护,并支付工资。
对比起我在国内医院门诊的第一年,当时在结核病控制中心轮转,每天在门诊收病人、给他们开化验单,从早上 8 点开始到下午 5 点,除了午休,一秒钟都没办法歇。但法国的医生是截然不同的生活节奏,他们每天的工作很轻松,除了公共假期之外,每年七八月份还是全国度假季,所有的医生都会去南法或者国外度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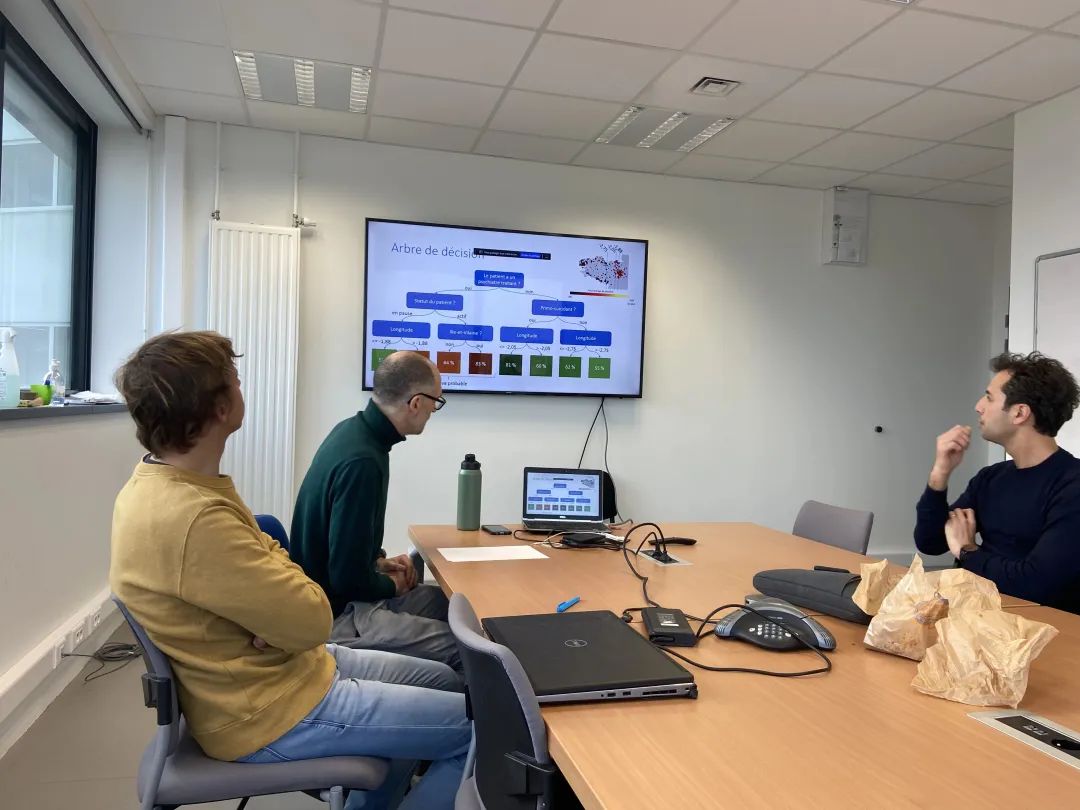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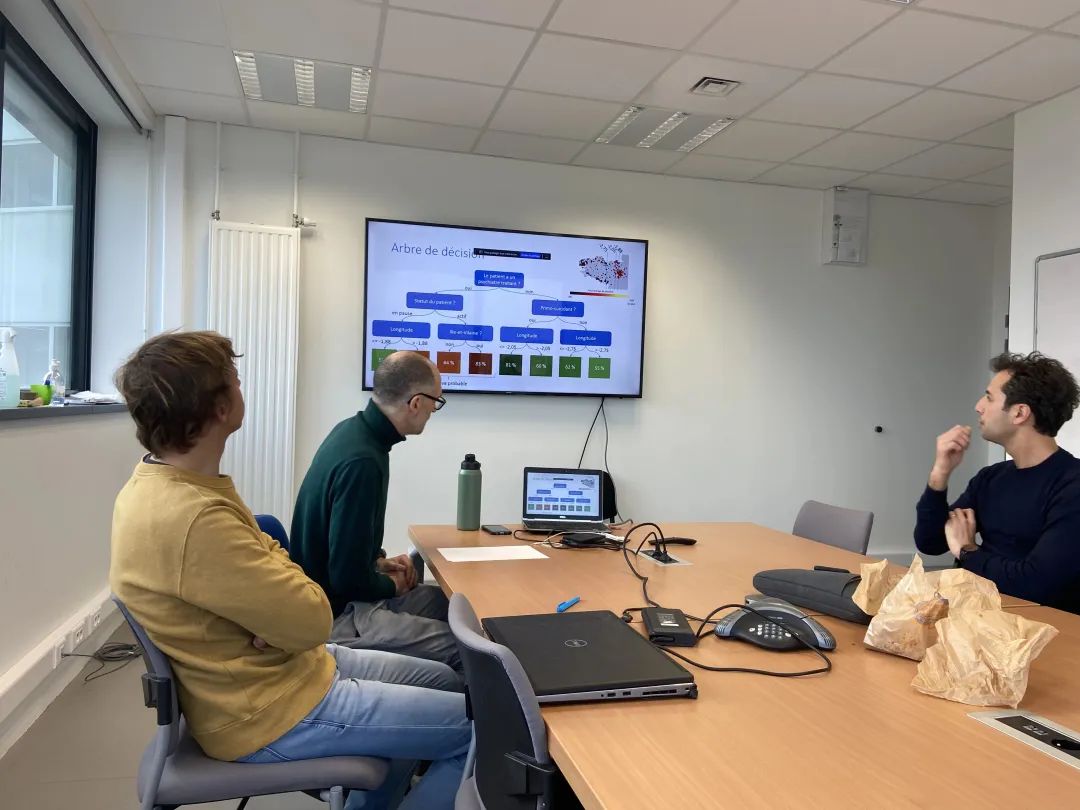


我在法国医院工作时的日常
03 回到「体制内」
医疗大数据,即「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机器学习模型的方法,去深入分析法国医院系统数据库的患者数据,它的应用场景很广,政府部门或大型的医院都有需要,博士毕业之后,我的薪资范围也从 2500 欧左右升到 4000 欧以上,法国的平均薪酬为 1750 欧/月。
将近 40 年的人生我做了很多决定,有对有错,但转行到医疗大数据是我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医学人工智能是行业的未来趋势,人才缺口也很大,风口被我踩上了。博士毕业后,我进入法国医学科研中心做博后,相当于法国的体制内。




在医学科研中心开会
兜兜转转,我还在搞公卫。我的年龄越来越大,对工作越来越安心了。
在法国的医疗体制下,医学生毕业即包分配,薪资待遇也很高,但毕业本身非常困难,9 年的临床医学课程中,每一年都会筛掉 50% 的学生,所以只要读出来,不夸张得说你就是「人上人」。也因此,博士毕业后刚来到医学科研中心时,我对和法国医生/医院打交道持乐观态度,认为他们都属于法国社会层面中的「精英」,合作将十分顺利。
但当我投入实际工作,却发现法国医院的行政效率大约只有国内的三分之一。以前在国内做综合医院督导工作,我一天就能去一家,一个月 20 多家不成问题,现在光联系沟通都很耗时。




我在医学科研中心的工作环境
举个例子,我上半年联系法国某医院的行政人员,一直未得到回复,只能联系该医院另一个人,他说这个行政负责人去休假了(法国人只使用工作邮箱,放假时收不到邮件,其他人也联系不上),要等她休完假。半个多月后我再次联系这个行政,却发现她已经离职,她也没指定谁来和我对接。
原本一周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最后被硬生生拖了两个月,《疯狂动物城》中树獭的演绎,真的不夸张。
当然效率的反面,是法国人的工作并不会很忙,就算在我博后期间也有充分时间满足爱好。业余时我做电影节媒体报道,做中法电影文化交流,戛纳,柏林,威尼斯电影节我都去过。




柏林电影节,我在采访
下个月,我将从博后出站,到巴黎另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做临床试验方法学家(Methodologist),这家医院相当于国内北医三院一样的头部三甲。临床试验方法学家主要负责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方法的前期设计,项目实施过程中监督项目负责人员对患者的纳入排除,后期监督数据管理人员对数据的收集和清洗,等等。
我对之后的工作很期待,不过最担心的还是正值 7 月(每年 7 月全法国各行业都放假)入职,不知道是否会因为同事们休假影响工作推进。




假期时,我喜欢在海边放空
法国政府给我的父母发放了 10 年长期居留,我把他们都接来巴黎居住,也为他们买了房子。法国是多种族国家,政府为移民安排了免费语言课,我父母每天跟着老师野餐、参观博物馆、逛集市,慢慢可以用法语简单交流。他们已经快 70 岁,但还在学习、还在前进,很感谢他们对我从小的影响。
现在,我可以说我活得「很舒适、很体面」。我和国内疾控的同事们仍在联系,在积极促进中法医学领域的交流。我手上也积累了一些项目,无论是留在法国还是去其他国家,我都有相当的自信,这是 20 几岁的我没有的。
我也会遇到年轻的医生来问我转行建议,听完我的故事后他们都会说「你有勇气,我不敢。」我也能理解。但我更觉得,不要给自己下定义,可以多一些选择,会给自己惊喜。这是我 22 年医学路最大的感悟。
本文地址:http://naizai.cn/archives/20301
以上内容源自互联网,由百科助手整理汇总,其目的在于收集传播生活技巧,行业技能,本网站不对其真实性、可靠性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特此声明!
题图来自Unsplash,基于CC0协议
